2023-09-23
白发悲歌—钱大妹
点击:次
白发悲歌—钱大妹

钱大妹的坟就在分水墩旁的泗河口村。很多年前,她的族人和儿孙们在几棵槐树旁埋下了她的尸骸。
泗河口村的1927年是不平静的。在长寿镇上开米行的钱大妹夫妇举家返乡,给村里孩子贫困无聊的生活增添了一些热闹。看着大人们三三两两围成一团,交头接耳的样子,他们好奇地凑到了钱大妹的家门口,睁大眼睛向屋内张望。在他们面前是小村里唯一的深宅大院,前后10间房子、两个院子,青瓦白墙,院后是一片葱郁的竹林。院子的空场上,花白头发的钱大妹正在和几个年轻人卸行李。孩子们认识她,一哄而上,把妇人团团围住,“阿婆”、“阿婆”叫得一个比一个欢。“阿婆”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许多花花绿绿的糖果,塞进一只只高高举起的小手里。
对夫妇的这次举动,村民们迷惑不解。那间米行生意虽然清淡了一些,但眼前这个年景里,规规矩矩做生意谁能发财?三个儿子、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,大儿子全荣又给老两口添了个活泼可爱的孙子。衣食无忧,儿孙绕膝,该满足了。他们不知道,钱大妹和老伴汤耀文早已加入了共产党,他们把米行建成了联络站。由于米行里人员往来过于频繁,引起了长寿镇长、恶霸地主陈祥安的怀疑。老夫妻商量以后,干脆关店返乡,想在分水墩建立一个更安全、更隐秘的联络站——钱大妹无法跟她的乡亲说明这些。

(钱大妹深夜沉思,完善行动计划)
几天后,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小村渐渐恢复了原状。村里人又为今年的生计犯愁,小孩子们也发现“阿婆”再也拿不出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。钱大妹进进出出,显得很忙碌,有时连那头花白的头发都顾不得梳理,散乱地披在额前。她家也总让人感到奇怪:白天大门紧闭,晚上敲过三更,门缝里还透出光来,走过大门口,能听到房子里嘈嘈切切,好像有不少人压低了噪音在讲话。这个年老的妇人确实没有歇着。有时,她自己想想都有些费解:年纪一大把,本可以安心地做老板娘,含饴弄孙,何苦去冒砍头的风险?但镇上保安团丁的残暴专横,地主恶霸的飞扬跋扈,左邻右舍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面黄肌瘦的贫民,又让钱大妹善良的心不能平静,她一次次地打消了这种念头。白天夜里,她和老伴刷标语、散传单,在峭岐茶馆、后塍街头都出现她步履蹒跚的身影;一个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地下党员,被秘密安排到她家,得到了母亲般的照顾……
钱大妹的黑发越来越少了,皱纹日渐一日地增多。村里的婆娘们总要上去关切地问寒问暖,说大妹你要注意身体,年纪不饶人呐。她习惯地捋捋额前的白发,微笑不语。
3月的一天早晨,早起的村民在薄雾中起床干活了。几个村民在经过钱大妹家后门口时,猛然觉得眼前少了些什么东西——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怎么不见了?原先的竹林里,胡乱地堆着些砍下的竹杈和竹叶,一片狼藉。一个村民猛地拍了下脑袋:昨天晚上悉悉嗦嗦的,是不是有人在砍竹子?深更半夜,要竹子干什么……临晌午时,从南边传来了消息,说不得了啦,出大事了,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围攻峭岐,拿着鸟枪、铁耙,听说,手里拿的最多的是梭镖,用竹子做的,头上削得尖尖的……
好几天后,钱大妹再次出现在泗河口村。家里已被陈祥安率领的保卫团糟蹋得满目疮痍。家产被洗劫一空,房门不见了,箱子柜子不见了,屋顶上残留着孤零零的几片碎瓦,屋前的空地上,留下一大堆灰烬,好心的邻居只从火堆里抢出了一张八仙桌。钱大妹伸出了手,轻轻地抚摸着桌面上火烧过的痕迹。村里人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,看着她微微颤动的嘴角,看着她头上翘着的几根银丝凝固在空气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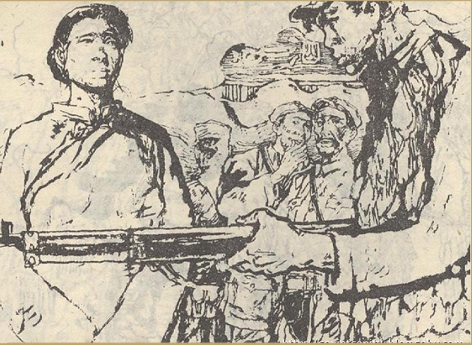
(钱大妹受尽酷刑,坚守秘密)
逃避回忆也许是抚慰创伤的唯一办法。以后发生的事,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陈述起来都是那么艰难。只在嘴边喃喃地说:作孽啊,大妹是吃了大苦头了!她可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妇人……1928年6月9日,钱大妹起得很早,匆匆地向村北走去。在周庄罗盛巷,她被捕了。
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整个泗河口村,善良的村民们无法预料这一天一夜会发生什么。这一夜,泗河口村特别的静。翌日中午,从镇上下来了几个保安团的团丁,吆喝着要钱大妹的家人交120元银洋、15石大米去收尸,黄昏时分,抬尸的人回来了。钱大妹的尸体轻飘飘地躺在担架上,上面盖着一床碎花被子,几缕白发从被角处垂了下来,在风中微微地晃动着。残阳如血,应天河水泛着鲜红的波光。汤耀文的脸上浮着一层奇怪的颜色,他木然地走在担架旁,拉着一个佝偻着的、削瘦的身影。
周围的人早已泣不成声。该给尸体净身入殓了。摆在几个老妇人面前的,已不是一具人的躯体,死者生前所遭受的凌辱和酷刑就印在这一堆骨肉的组合体上。她的衣服成了几片破布条,遮不住全身,由于血流得太多,布条都被泡透了,时间一长,硬绷绷地粘在身上拉不下来。这个老女人的稀疏的银发被血染成褐色,不规则地缩成几团。全身上下,都是鞭子抽过留下的血痕,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,手指尖、脚趾顶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针眼。两只下垂的乳房上烫着铜板大小、焦黑的烙印、外阴部血肉模糊,鼓起一个一个水泡,像是用烧烫的硬物截过……

(钱大妹坚贞不屈,英勇就义)
为了年轻人的未来,这个年长的妇人死了。
她的一生正如流淌不息的应天河水在分水墩毅然向南流去的那支,变得那么清澈、那么轻柔……
许多年后,我来到烈士的家里,只找到了那张曾被扔进火堆的八仙桌,上面的烙痕犹存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它,像钱大妹当年一样。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,后人才能和她的心灵有一点默契。
钱大妹坟前有几棵老槐树,枝繁叶茂,在暖暖的阳光下闪动着斑驳的光点。轻风徐来,老槐树发出“簌簌”的声响,仿佛在与烈士窃窃私语。

